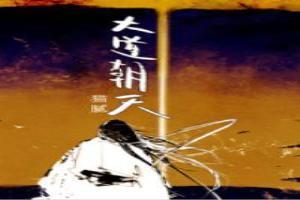距大軍開拔已過半月,仲冬時節,邊關之外,廣袤的瀚海一片冰封景象。天際的雲濃稠而厚重,像隨時都可塌壓下來。
黃金王帳里安了四隻掐絲琺瑯三足熏爐,煙氣裊裊,隔絕了外頭的天寒地凍。美人榻上的人怡然橫臥,手中銀角杯輕輕一晃,晃出一滴清冽酒液來,恰落在他的唇角,被他伸舌舔去。
有士兵前來傳信,吭亮地道出一聲:「報——!」銀角杯因此晃過了頭,一滴酒液順著他敞開的衣襟滑落,緩緩划過和田白玉一般精緻無瑕的胸膛。
卓乙琅惱了,卻只是皺過一下眉頭便恢復了漠然的神色:「大驚小怪。」說罷起身,隨手丟了杯盞,踱步到几案邊,「說。」
那士兵頷首答:「啟稟世子,我軍東西南北四路輜重當中,有三路分別於昨夜子時、丑時及今辰卯時遭劫!」
卓乙琅聞言稍稍一愣,隨即笑了一聲,垂頭瞧了眼几案上鋪陳了的一幅尚未作成的畫,想了想揀了支筆,給畫上人添了一道眉,而後道:「燃眉之急,燃眉之急啊。我軍空駐此地半月,給那些俘虜來的廢物供吃供喝,糧草頻頻告急,如今三路輜重被劫,當真燃眉之急也。」
那士兵皺了一下臉,聽懂了這個成語。的確很緊迫啊,可世子您的語氣能不能與您說的話稍稍對上點頭呢。
他在原地靜候指示,半晌才聽卓乙琅語聲清淡地繼續道:「未被劫的是哪一路。」似乎也聽不大出詢問的口氣。
「回稟世子,是東路。」
卓乙琅彎了嘴角,再在紙上落了一筆眉:「時辰間隔如此相近,他大穆皇太孫是有三頭六臂不成?」
士兵不知此問是否該作答,默了半晌沒聽見下文,只得硬著頭皮道:「或許是的,世子。」
「蠢。」他虛虛點一下他,「一個人只有一顆腦袋與兩條臂膀。所以你猜猜看,他究竟身在哪一路?」
士兵將西南北三路猜了個遍,才聽卓乙琅嘆了口氣:「如此腦袋,如何能與那些狡猾的漢人較量。我方才不都問你未被劫的是哪一路了。」
他霍然抬首,神色震驚:「您的意思……!」
「東路的輜重為何沒被劫呢?那是因為大穆的皇太孫勞心勞力,躬身替我送糧草來了。他若不留一路活的,如何曉得我大營的位置?」他笑笑,將作成了的畫一點點收攏,「好了,你下去吧。」
那士兵撓撓頭要退下,走到一半復又回身:「卑職斗膽再問一句,您當真不作指示嗎?」既然都曉得敵人在哪一路了,怎得還一副要等人家直搗黃龍的模樣。
「我自有打算。」卓乙琅似乎脾氣很好,心情也不錯,並未因此動怒,待人退下才捏了畫出去,走進一間關押俘虜的帳子。
帳子裡散發著一股腐臭的氣息,昏暗而潮濕。他揮退了守值的將士,望向蜷縮在角落,被手鐐腳鐐束身的人。良久後親自掌了燈上前,伸出一根手指將那人沾了灰泥的臉擦拭乾淨。
灰泥一點點卸落,明黃的燈火映照著那人的臉,慢慢現出一張與卓乙琅一模一樣的面目。
他扯了下嘴角,淡淡叫了一聲:「兄長。」見對方神色疲倦地閉著眼,絲毫不出聲搭理,只得再嘆息著道,「兄長,還有最後一戰。」
他說罷一抽綢帶,展開了手中的那幅畫:「殺了此人,這些年你虧欠我的便還清了,你的未婚妻也將得到自由。」
他交代完便彎了彎嘴角,將畫丟在一旁,起身掀開帘子走了出去。
一個人的確只有一顆腦袋與兩條臂膀,可他不是。
……
貴陽下起今冬第三場雪的時候,納蘭崢窩在書房裡翻閱案宗,手邊是一隻銅雕錦地龍紋八寶手爐。那些案宗都是拿湛明珩留下的印信調來的,雲戎書院裡頭不教這些,因而她不大懂,得重新學起。
聽見叩門聲,她翻過一張書頁,頭也不抬地道:「進來。」
湛允抱了一堆文書來,多是些用以學習琢磨的範本,給她擱下後詢問是否還有旁的需要。
納蘭崢這才抬起頭來,說:「我看了近些年有關貪墨案的案宗,倒有一個想法,卻不知是否可行。」
「您說說看。」
「貪墨案須經三司會審,其間環節複雜,三轉四回,經手者眾多,而三司裡頭必然有豫王爺的暗樁,尤其公儀閣老掌管的刑部……」她說及此一頓才繼續,「因而此次押解入京的犯人未必最終皆得懲治。豫王代理朝政,要動手腳保人再輕易不過,恐怕證據一進三司便會被銷毀。咱們殫精竭慮處理完後續,便是為避免湛明珩來不及收拾的爛攤子給朝臣們留下話柄。但倘使『抓錯』了人,恐怕適得其反,還得叫他們說一句太孫處事不周。」
她說到這裡停下來想了想:「咱們如今最大的劣勢,一來天高路遠,二來我明敵暗。因此……何不先交一份假罪證去探探虛實呢?」
湛允眉心一跳,這個想法,不能不說極其大膽。
但納蘭崢卻面色不改地說:「只有藏下證據,先遞交一份假的上去,才能瞧清楚究竟哪個環節安插了對方的人手。如此一來,他們能保人,咱們也能翻案。光明正大是拿來對待君子的,對待小人……算人者,人恆算之。」
湛允想了想,應道:「屬下這去辦。」
這邊方才解決了貴州貪墨案的事,湛明珩便與卓乙琅正式開戰了。納蘭崢為此日日提心弔膽,卻是尚未得到前線來的捷報,先聽聞了朝堂的動靜。
八百里加急送來的密報,說是朝議時,一干文臣紛紛義憤填膺地參了太孫一本,稱其違背聖意,為一己私利劫掠狄軍輜重,主動挑起與狄人的戰火,實在年輕氣盛,難堪大任。
納蘭崢著實氣得不輕。
卓乙琅的確是聲稱要與大穆談判的,因而朝廷不曾下達開戰的指示,湛明珩領去邊關的所謂大軍也並非驍勇善戰的生力軍,而是臨時徵調來的地方守備,為的是替他保駕護航,和談不成才動干戈。
只是但凡有眼睛的都該瞧得出這誘敵深入的計謀,如此情狀,倘使不能夠先發制人,便等於是叫湛明珩去送死。
他去了,如今他們卻反過來參他一本,明里暗裡說他爭強好勝,欲立軍功,視聖意若無物,置黎民蒼生性命於不顧。
可如今的朝堂哪裡還有聖意呢?所謂聖意,不過是代理朝政的豫王的意思罷了。
她捏緊了手邊的杯盞冷笑道:「這些個朝臣如今倒是不在乎大穆的顏面了!當朝王爺被人砍去了雙臂,當朝太孫以身犯險前往交易,他們竟還能夠好聲好氣地請求和談。湛遠鄴究竟給這些人灌了什麼*湯藥!」
湛允亦是恨不能飛奔回京插湛遠鄴幾刀子的模樣,一拳砸碎了一張椅凳:「不僅如此,朝臣們鬧得不可開交之時,還是那狗賊替主子收的場,當著滿朝文武的面,稱將派援軍助太孫一臂之力,既然太孫主戰,便必然有他的道理。如此假仁假義,實在用心險惡!」
納蘭崢冷靜了一會兒,擺擺手道:「現下談論這些也無意義,朝堂之事你我鞭長莫及,只得待湛明珩回來再議了。」她說及此處語氣和緩了一些,「邊關那處可有消息?此前軍報說他暗中跟隨狄人的輜重隊直搗敵營,現身時僅僅八百精騎……我看他也是瘋了。」
湛允剛欲答話,卻聽外頭廊子裡有人步履匆匆行來,到得書房門前喝一聲:「報——!」他見狀上前接過軍報,只一眼便是面色一沉。
納蘭崢坐不住了,緊張地站起身來,急問:「可是湛明珩出了什麼岔子?」
他搖搖頭,神色卻沒有絲毫的鬆懈,緩緩道:「……西境破了,三萬狄軍秘密越過四川,直向貴州省境而來。」
納蘭崢身子一晃,險些要栽倒下去,扶了桌案才堪堪穩住。
這是一則極其矛盾的軍報。多達三萬的敵軍,如何可能悄無聲息地入關,一路暢通無阻,秘密穿過那麼大一個四川省,直至接近貴州省境才被發現?顯然是大穆邊關守備出了問題,有奸細放了行。
四川省在父親的右軍都督府管轄之內,竟也被湛遠鄴輕易地架空了。
她白著臉沉默了半晌才問:「領軍人是誰?」
湛允神情嚴肅地搖搖頭:「尚未探知。」
「不論是誰……都是沖我來的吧。」
湛允掙扎許久,忽然掀了袍子跪下來,道:「照如此行軍速度,不出三日敵軍便可抵達貴州。納蘭小姐,您……您跟屬下走罷!」
她一動不動地盯著他,良久後反問道:「走?我的腳下是大穆的土地,我能走去哪裡?我往東走一步,三萬敵軍便愈往大穆腹地進一步,你叫我走去哪裡?」
他知說服納蘭崢不是容易的事,只得咬咬牙接著道:「不瞞您說,主子臨行前除卻印信,還留了一塊虎符在屬下手中。那虎符是陛下在京時及早交給主子的,可調動貴州全線地方守備,您與屬下先且東撤,此地自有將士們守牢。」
納蘭崢點點頭: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但是湛允,你在保護我之前,首先應當記得,我是你的主子,但也是大穆的臣民。」
她說到這裡已然恢復了平靜,將那封軍報捏在手裡看了看,說:「將貴州全境的地方守備圖拿一份給我。」
湛允錯愕地抬起頭來:「納蘭小姐……您這是要?」
她沒有看他,只說了兩個字:「守城。」
第65章守城